︎Training Core
Interview with Liping Ting: The Poetry is Now
訪談丁麗萍:詩歌就是當下
敘述/丁麗萍
採訪、英文編輯/雀榕
中文編輯/Calm Computer
English Version coming soon

丁麗萍演出作品《WISDOM • TRAUMA I. (Hair•Dharma)》
於2024卦山力藝術祭,彰化市 |照片來源 鄧婷雯
於2024卦山力藝術祭,彰化市 |照片來源 鄧婷雯
詩人在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自古以來世界各地口頭文學文化中,均有民間吟遊詩人的傳統。詩人吟唱敘事並傳承民間勞動生活與情感故實。有如詩經國風民間集體創作,中亞細亞、 高加索民間古調、歐陸中世紀的 troubadour、非洲歌舞藝人 griots,詩人用吟唱的方式來敘述民間生活。
每次有重要的祭典時,吟遊詩人是族群民間慶典祭祀不可或缺的族群故事的吟唱者。相較於宮廷在朝文化的雅頌,在野的民間詩人傳遞著一種介於文化與神話之間的敘事力量。而古希臘詩歌 poēsis 意涵詩歌即是藝術創作,詩人在族群生活事件擔任傳承載體的角色的同時, 也意涵詩人始終承擔某種族群生活的社會文化責任。
我曾經在幾次音樂學旅途中,切身地與當地詩人詩歌相遇,透過接觸不同文化行徑的族群,進行類音樂學的田野探索。1998年,我與實驗音樂領域的朋友,很單純要認識「他者」的音樂文化,追尋一種非學院的,但真實地民間相遇。我們去了中國貴州拜訪苗族侗族,及其他當地原民的當地音樂文化 ,如在侗族村落,結識了村裡的音樂家及耆老,每到夕陽暮色,就靜待在他們所建,聯結村外村內的橋面上,聆聽侗族族群先慢慢抽起煙,再不徐不緩地慢慢吟唱他們的複音古調,也深究他們對於空間,建築與戲曲音樂之間的觀點。侗族有非常重要的複音音樂文化(polyphony),村子中心的穀倉就是他們的劇場,也是居民常常聚會賞戲的地方。
另一侗族村裡的婦女們會在河邊一邊洗衣服一邊吟唱,他們說,曾經有西方人來到這裡錄音。你們到民間市場就可以買到我們的卡帶。於是我們去市場買了些卡帶回來播放,卡帶裡紀錄的是一個大型祭祀的族群共歌的聲音,婦女們聽了都興奮的喊著:這是我的聲音!這是我的聲音!民間音樂裡充滿活力、粗獷、優美、細緻的感受像是都收錄在這張卡帶裡了,咔咔咔滋滋滋,音質非常差,大家圍繞在一起聽,村民仍能認出自己的聲音,民間音樂如此純樸熱情。
更遠村落市場上遇到一位擺地攤,賣書賣雜誌,寫詩的侗族老詩人,他收集了很多雜誌,也有自己的詩歌創作,他希望能透過創作,讓自己族群的文化歷史能傳承下去。
在您幾次表演中,聽到同一句話出現:Poetry is Now。這句話對你來說有什麼意涵?
Poetry (詩學)的字根 poesis 本身的意涵就是創作,是所有哲學,所有思想的總籌。音樂和詩歌對我來說也都是廣義的詩的意涵,而所有創作活動跟我們生活有關係。 Poetry is now 1 是一邀約,來共同審視批判當代現況,地球村存續危機,迫切的詩的行動。
從達達、50年代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等運動的進程中,詩變得更民間化與口語化,更能吟唱。對我來說,達達的聲音詩、行動詩都是重要的美學運動,和社會革命有直接的關係。他們反戰,對戰爭批判。達達反戰是以啞啞學語和無意義的生字,進行一種反諷、嘲弄、悲傷地反戰。
近期我重新審思這些運動史的脈絡,包括我受邀參與由陳怡君編劇王墨林導的《黑色-在詩與革命之間遊走的黑色青年》2 實驗劇場創作計畫,從中認識到臺灣中南部的詩人賴和以及當時百年前在日治時期下不能發聲的詩人,他們的行動同時是劇場也是政治運動,包括無政府和共產主義者用不同的理念方法運行。面臨運動中的紛爭,賴和的詩則是充滿共同合作的能量,充滿對普世的關懷,希望團隊不要再分裂,真正負起對這個世代的責任。
當我把百年前歷史社運的改造者和詩人時代變革中所做的詩作,再次詮釋的時候,那是相應於當代社會有這個需要,而不是屈就於混淆的僵化的意識型態之爭。參與黑色合作創作過程中,我個人認為引用先人的思想事件的時候,都必須在創作的當代「現場」,同時審視我們當代的需求,活化其歷史的意義,而非止於僵化的紀念碑呈現。歷史事件只有重新活化重新被感知,才能重新存在當代。

丁麗萍 |照片源自 2009年法國巴黎Ephemère詩歌節7x7詩歌活動
能聊聊您對「演出」和「現場」的看法嗎?
我在音樂會上,在戶外公共場域 ,在日常個人生活場域, 都可以進行行動藝術現場,而非演出 。因為「現場」實質,有實驗和不斷向前超越的精神實質在裡面。凱吉和老莊的思想都不傾向給任何事物命名,將其設限變成一個既成僵化的結果。
試想我們是否有時也會被自身文化偏見限制,混淆理解「現場」「演出」? 如果回到情境主義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的思考,沒有什麼所謂「演出」,真正的事件,可以在街頭上現場發生。事件現場就是一場運動,美學運動就有社會運動訴求。詩歌行動做為美學行動,就絕對不是為了要媚俗演出、成為資本社會的一個預設成功的結果。
過往我曾在巴黎合作主持一系列,多向度的群體創作實驗活動,如TOPOPHONY實驗運動 ,如INFORMO實驗期刊 ,如藝術節INOUIR3 。自此,我始終堅持個人浪漫的理念:創作者必須活生生地,一直在實驗活動現場創作當中,不去為了成功結果來設定追索創作。

Topophony實驗運動現場 | 照片源自丁麗萍官方網站 https://www.liping.fr/topophonie.html
在您的演出中,能感受到不同感官的交織同時,一種整體性的生命體現。你是怎麼對待不同的感知表達?
對我來說,視覺和聽覺等感知是同時存在的,從來沒有界限。而劇場永遠都是廣義的生活感知總匯,凱吉音樂思想論述提到,在他重視的西非族群社會結構中,祭典像是一種現場對話,用舞蹈、音樂、敘事詩來處理族群之間的紛爭。由此反觀,今日風行的跨領域風潮,則在民間劇場的傳統中早已存在。
我早期作品也以祭典結構呈現,以祭典呈現作品的精神價值。而世界各地的民間祭典,充滿聲聲色色,有不同方式的參與,不同形狀的時間性。西非多元族群的祭典在每一個族群裡,都有每個族群不同的生命哲學,比如西非巫毒教的喪禮,有些族群喪禮悲傷,也有族群兒子為死去的父親跳舞送行,即使個人內心很悲傷也要向族群展顯快樂去捨離。
1999年所創作的《九九行動 Actions 99》4,就是一個祭典性的當代作品。我意圖要打破觀者和被觀者,盲人和非盲人之間的界線。希望讓非盲人透過盲人的指引,打開之間的界線同時,兩者都能感受到美學和生命的存在。當時美學的形式的確就像現在所謂的「沈浸式」劇場。其中有一個時間點,我在黑暗中舞蹈,所有觀眾都是背對著我,我在舞蹈過程中所發出的聲音、呼吸、感觸,期待讓他們能在心裡頭看到,用心用感知來看。觀眾都在極端的黑暗當中,感受空間裡不一樣的路徑,在過程中我們彼此也共有一個祭典,希望達到盲而心不盲,讓觀眾成為引導者,也是我的共同創作者。5
觀眾對你的創作來說是什麼角色?
觀眾是我相當重要的創作條件,他們是審視者(witness),我的支柱,身體、精神,文化、存在環境的支柱,沒有觀眾,行動現場沒有社群共享共創意義。他們是我精神上、身體上的背景,以及存在的處境,這處境也隨時在變化。
2000年我在法國南栖城近郊 Festival Musique Action 所創作的三人合作作品《Karkass》6 中,將觀眾都請到舞台上,再將全部的燈都關掉。我在非常黑暗的空間使用微小手燈,用光去刺激觀眾,反應冷戰時期用光懲罰罪犯的歷史。我以詩人的方式提出很多問題,用身體接觸觀眾,他們就在現場中間,而我在其中圍繞和穿越。現場有一位貝斯手和電吉他手正在演奏,聲音非常大,在極端噪音當中,我嘶吼、質問。我開發不同情境,即使現場沒有門,我創造了一扇門的情境。我問觀眾,這扇門為什麼要關起來?不打開這個門。對我來說這些都是詩歌在現場創作的狀態。或許大家也沒聽懂我在幹嘛,問了荒謬的問題,但都覺得非常有趣。我經常在這樣黑暗中進行,這對我來說也像是一個祭典,產生許多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生命質疑,我想跨越心盲與心不盲之間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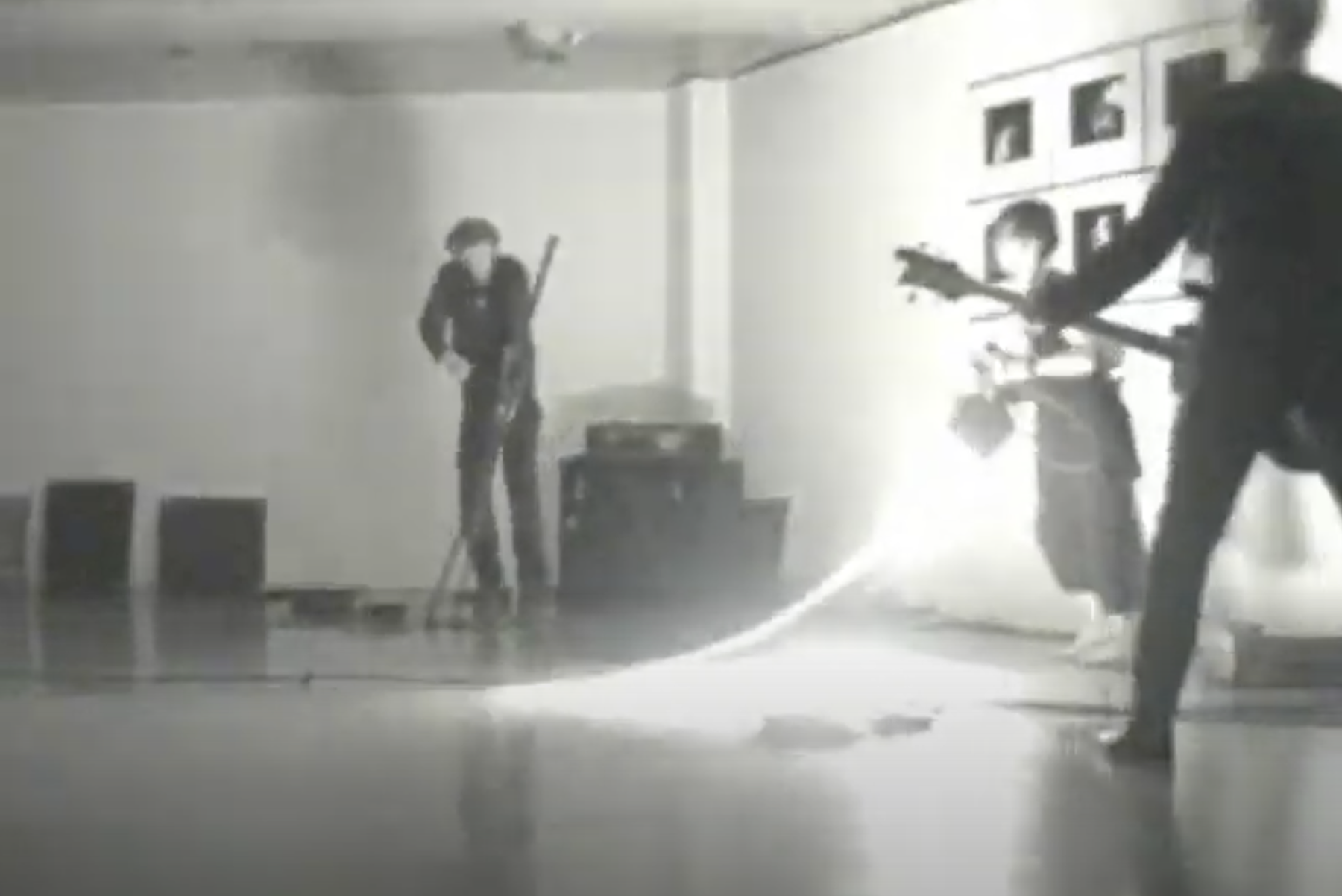
丁麗萍、Arnaud Paquotte、 Olivier Paquotte三人合作作品《Karkass》,Festival Musique Action, 法國2022 |影像源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51pASxeuU
1998我在巴黎的一個學校廢墟進行現場活動,這裡廢墟是由無家者非法佔領的,藝術家們共同參與一場由無家族群舉辦,在階梯教室進行的藝術活動,我拿起雨棒,從教室最下面的平台,試圖穿越塞滿著無家者觀眾的階梯教室。我不言不語,又是女性又是外族亞裔,他們全是男性、身體粗獷、發臭,我用聲音和身體慢慢穿越他們之間的縫隙,觀眾對我充滿疑問和不解,他們沒有搞懂為什麼一個演出是這樣活生生在他們當中行動。他們充滿著問號,不信任感,而我必須堅持意念得到他們的信任,這樣的狀況其實是相當危險的,最後我穿越了觀眾與人群,也得到他們的歡呼,我在現場的創作就這樣與觀眾一起共時存在。
另一次的經驗是在2003 Irtijal 黎巴嫩的即興音樂藝術節7,內戰後村裡很多成年人都去富裕的阿拉伯國家工作,鄰居之間並不怎麼說話。藝術節邀請我們到山上去村里進行一個現場,所有村落的人興奮地帶著自己家的板凳來看現場,大部分是村落的孩子與年長者,大人們找來柴火生火,我就跟他們學了當地語言的五個字,金木水火土,每當我說一個字的時候,我也指出現場的一個金木水火土物件,孩子就狂熱的叫囂尖叫,充滿喜悅與熱情的說他們也要參與,一種很無政府的狀態。他們沒有過這樣的音樂現場。他們一直站起來,想要參與即興,而村子裡的長者又一直叫他們坐下,孩子熱情更欲罷不能。
事後深思這些經驗都好像在銜接什麼被漠視的文化角落,面對我出生的環境,來自知識分子的文化,而生長家庭環境清寒,生長的地理人文更是文化沙漠等。我在這內戰後的他者文化偏僻村子,創作行動中因孩子熱情感動喜悅,有如真實的民間生命力激發我無限的驚嘆、驚喜!
曾經有一篇報導提及了你涉及冥想相關的訓練,能多說說這方面的身心實踐嗎?
我曾經深入一個古生代壁畫岩洞,法國農夫兄弟在耕田的時候發現家族田地下的大山洞。要進入這個空間必須穿越許多廊道,越來越窄,當中有冰柱還在滴水,水滴形成一個小湖泊。整個空間的結構很像子宮,穿過窄小的路徑進去後還有更細聲的水滴聲音,形成更小的小湖泊,在這個洞穴裡的水滴聲音層次更顯清澈,如同無限迴盪的繞樑三日。
我曾深入泛音歌唱 (Overtone Singing),以泛音回聲來暖化五臟六腑,也同時練習太極的基本功,進行寂靜冥想,透過靜語去聆聽所有存在的聲音。
靜語在佛家、老莊思想裡都是相通的,透過寂靜讓時間空間更廣更深。這和太極拳裡面所說的的運功一樣,運功中通過一個人的精氣神,來達到「神」的境界,透過你的智慧與意念來深化自己內在的空間與時間。

丁麗萍與太極| 照片源自丁麗萍官方網站 https://www.liping.fr/worksinsitu.html
我在練習雙聲複音時,借用太極拳裡精氣神的意念,讓聲音在腦中迴響,在吐納之間想像我是山水或是岩洞,通過聲音在我的身體內發聲與暖身,同時也在檢視自己。像是打太極拳在前後宇宙間畫出無限(∞),透過呼吸與想像力,達到「神」的境界,試著在心裡頭看到自己存在的狀況,你的神就是你的精神與智慧所在,要達到這個境界,需要每天的練習。你一直呼吸,一直活著,如何引領你內化自己的山水,或許是畫裡的山水,或許是你曾經去過的地方,甚而是抽象純意境的詩歌情景,透過靜語和呼吸,邀請這些山水內化到你自身的內在。
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美的內在功夫。或許是你上次旅行的經驗,或是現在和我在這邊交談的當下領悟,將來可能又有一個山水融入你原有的山水裡面,你就是一直在準備這件事,一直繼續內化,繼續創作山水,再生山水。
這些內化山水,會讓你的意念自然轉化為雋永的詩句一樣的意境,不管是惆悵、寄託、或是願景,當你成為詩人的時候,你就是正在創作,能夠內化也能夠反應外在,這並不是天地人合一不可說意境,而是創作的主體已經準備好了。自由了,沒有任何框架,對外隨時可建立社會關係,無論是人、自然、景物,存在環境、城市環境、社會事件,他內化成為主體,有相對的能力可以同時在這些關係中交織和存在。
對內實則如海德格詩學裡的邀約,詩人如何存在這個世界上,知道自己存在的狀態,在哪一個存在方位,當你山水內化的時候,你就有整體的創作能量了。
我的生命整體也是一個生態圈
在疫情之前,大家開始注意到全球暖化以及生態詩的創作,生態詩關注民主平等的思想,以及所有生物的平等。哲學家阿恩・內斯(Arne Naess)早期的哲學很重視東方思維,老莊批判與儒學結構化的思維,或者可以說,老莊思想讓潛能存在,擴大等待的領域,觀審整個自然和所有的生命。
這個地球上的所有東西都跟我們有關係,我像孩子一樣貪心,希望把東西都放在一個籃子裡面,裡面充滿各種的色彩,我希望用民主的審視,每個色彩都是平等的,都是他們自己的色彩。如果美學上已經進展到永續生態與生態詩歌這些概念,那麼大家都在同一個地球上,共同討論事情,也是人類學最重要的願景,所有傳統和當代文化的共存,每個文化都有它的特色以及它當前的需要。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的身體,我的感觸,我的生命整體也是一個生態圈,每個生態圈都會受到不同影響。我的背景、文化、以及我成長的年代中所接觸蔣介石時期的政治思想。大學的時候,我的老師們都是西方學院出生的,他們希望能以中西的比較哲學,重新詮釋老莊思想,重新看古代文本。「哲學」一詞源自於希臘,而東方則是用思想來代表人文發展,這兩個不同的脈絡要如何比較?如果站在地球共存的角度,我會以宏觀的視野,再去細看微觀的世界,如何才能達到真正的平等,不再以人的視角看自然,回到審視這個地球,我們共同生存的未來可不可行。
文獻參考
[1] ‘Poetry is Now’ 源自1946 兩位達達詩人的合作創刊共同理念,彰顯其對時代迫切的詩歌行動_Poetry is Now_PIN_Kurt Schwitters & Raoul Hausmann, 1946. https://www.academia.edu/25697771/The_Thing_about_PIN
[2] 《黑色-在詩與革命之間遊走的黑色青年》項目介紹和報告劇的影片節錄:https://archive.ncafroc.org.tw/result?id=7950319742a44aa6a0724861b884a3f3
[3] 丁麗萍從1988起至2013年定居於法國,活躍於巴黎 Topophonie 音樂與視覺實驗團,究竟戶外公共藝術,與環境聲音實驗。2002-2008之間,麗萍共同主持跨領域藝術出刊 « InFormo» 並持續年度舉辦'In-Ouïr 跨領域藝術節 至2012年。https://www.liping.fr/topophonie.html
[4] 丁麗萍的藝術計畫 «九九行動»- Actions99 就殘障盲人的視障局限與人對黑暗本質,發出終極關懷 - 盲人帶領非盲人即正常人經歷漆黑的建築裝置,完成黑暗中光影互動,及人性強勢與弱勢可以黑暗中相互扶持的寓意。
[5] 丁麗萍加註:此計畫也呼應著海德格哲學的後期思想,邀約詩人回歸大地棲居,回歸人存在的本真,而詩歌的本真,就是詩人在黑夜中吟唱,傾聽大地存在。
[6] 《Karkass》為丁麗萍、Arnaud Paquotte、 Olivier Paquotte 三人所創作的演出作品,2012 初次發表於法國東北部維萊萊南錫的 Festival Musique Action。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51pASxeuU
[7] Irtijal音樂節創辦於2000年,目前是貝魯特市歷史最悠久的音樂節。其音樂範圍廣泛,包括實驗音樂、自由爵士樂、自由即興創作、當代音樂、噪音和自由搖滾以及其他形式的創新音樂創作。https://irtijal.org/
(Update: 2025-05-12, This Interview Articles form lololol “Energy Index”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 LIPING, TING
Interdisciplinary artist born in Taiwan. Liping studied Philosophy at Taiwa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earned her Master in Theatre Education from Paris III Sorbonne Nouvelle. She lived and worked in Paris from 1988-2013 and returned to Taipei in 2013 for artist residency, and continued artistic dialogue, reflection on her experiences in Europe and a return to the philosophy of Zhuang Zi. Liping’s work maintains a focus on music improvisation and sound experiement, and often collaborates with contemporary poets, musicians and performance artists.
Interdisciplinary artist born in Taiwan. Liping studied Philosophy at Taiwa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earned her Master in Theatre Education from Paris III Sorbonne Nouvelle. She lived and worked in Paris from 1988-2013 and returned to Taipei in 2013 for artist residency, and continued artistic dialogue, reflection on her experiences in Europe and a return to the philosophy of Zhuang Zi. Liping’s work maintains a focus on music improvisation and sound experiement, and often collaborates with contemporary poets, musicians and performance artists.
︎ 丁麗萍
當代藝術工作者,台西長大。政大哲學與巴黎三大戲劇教育碩士(研究 Beckett 劇場及Cage 當代音樂)。巴黎工作多年 (1988-2013),2013年台北駐地創作,繼續藝術論壇,反芻歐洲經驗,重回莊周思想。其創作始終關注於音樂即興、聲音實驗,常與歐美各當代詩人、當代音樂作曲家及行為藝術家互惠合作。
創作理念以人聲探索出發,哲學思維中堅,詩歌行動落實,究竟人文與環境聲音實驗,就人生存不安本質,與面臨混沌黑暗生存環境,尋求藝術反詰,關懷與實踐!
https://www.liping.fr
https://vimeo.com/lipingliping
當代藝術工作者,台西長大。政大哲學與巴黎三大戲劇教育碩士(研究 Beckett 劇場及Cage 當代音樂)。巴黎工作多年 (1988-2013),2013年台北駐地創作,繼續藝術論壇,反芻歐洲經驗,重回莊周思想。其創作始終關注於音樂即興、聲音實驗,常與歐美各當代詩人、當代音樂作曲家及行為藝術家互惠合作。
創作理念以人聲探索出發,哲學思維中堅,詩歌行動落實,究竟人文與環境聲音實驗,就人生存不安本質,與面臨混沌黑暗生存環境,尋求藝術反詰,關懷與實踐!
https://www.liping.fr
https://vimeo.com/lipingliping